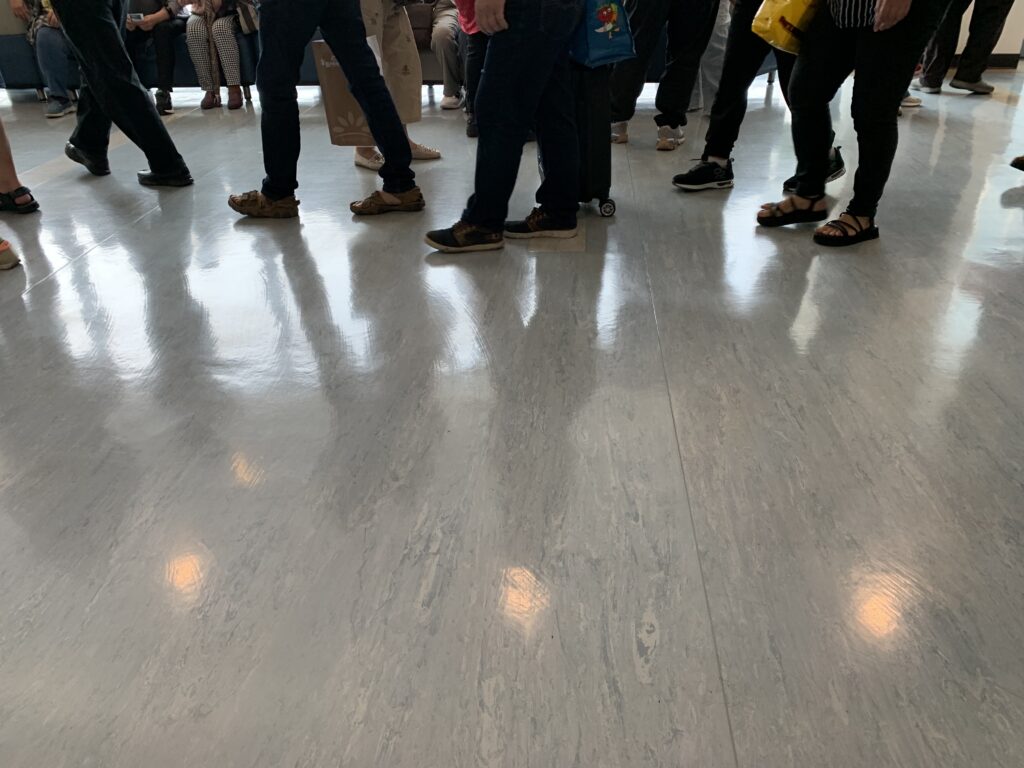
「轟隆~轟隆~轟隆,唧——」
一輛擠滿人的火車駛進月台,列車煞車時,車裡的人也跟著慣性前後擺動。原本杵在月台上忙著自己事情的候車旅客們,瞬間變得目標一致,手忙腳亂地準備往車子衝。
有人在月台販賣部買來點心,吃到一半,連忙用橡皮筋綁住包裝袋,再塞進行李裡;有人趕緊把屁股從行李袋上方挪開,拎著還留有肉體餘溫的行李擠上火車;有人右手拖著行李箱,快步走向最靠近的車廂入口。
我的視線,卻一直緊緊盯著一個底部有輪子、沿路發出「叩、叩、叩」聲音的行李箱。四個邊角裝有小滾輪,上方拉桿還能帥氣拉出來又收回去,看起來就像一台隨身小貨車,也太方便了吧,難怪那位路人阿姨可以一邊輕鬆地拉著行李,一邊扯開喉嚨罵小孩。
轉頭回來看看放在媽媽腳邊的行李箱,也是不錯啦,原本是兩層的中型行李袋,只要把上方跟旁邊的拉鍊個別拉開,就能瞬間加長又加寬,變成三層的大行李袋,足夠放下一家五口的衣服。可是,這行李箱底部沒有滾輪,要我跟哥哥、姊姊三個人一起提著,提久了真的好累啊。
「媽媽,我們也買那種會叩叩叩的行李箱,好不好?」指著從眼前經過的滾輪行李箱,我問。
但媽媽似乎沒聽到我說的話。她左臂抱著小嬰兒弟弟,不斷察看右掌裡的車票,心神不寧地在月台東張西望,嘴裡喃喃自語:「為什麼往臺東呢?不是往枋寮嗎?」
停在我們眼前的列車,外頭寫著大大的「往臺東」。雖然我們已經站在最靠近列車入口處的月台上,但媽媽不敢貿然上車,眼神著急地尋找哪裡有往枋寮的列車;而月台上其他旅客則在一聲聲的「借過」下,擠過我們一家,紛紛跳上了火車。
發現媽媽好像很慌張,我跟姊姊也彷彿被感染情緒,瞬間變得很不安,兩人緊緊抓著媽媽腳邊行李袋的拉把。管他行李箱會不會叩叩叩,有沒有輪子,有沒有拉桿,都不重要了啦,媽媽怎麼了呢?為什麼她不帶我們上車?
列車裡擠滿了乘客,他們透過玻璃窗看著還站在月台上的我們,我們也看著他們。鳴笛響起,他們的臉隨著列車的搖晃,轟隆轟隆轟隆,慢慢地駛離我們的視線範圍。
原本站滿旅客的月台,此刻就像螞蟻窩突然被一盆水沖刷過,螞蟻們紛紛朝四面八方散去。偌大的月台空間,只剩下抱著小嬰兒弟弟的媽媽、十歲的哥哥、八歲的姊姊,以及五歲的我。
現在……該怎麼辦?為什麼不上車?我們要去哪裡?
那是冬日中午仍有豔陽的舊高雄火車站。剛從刮著冷颼颼東北季風的澎湖搭半小時飛機過來,身著厚長袖的我們,現在全身都冒著熱汗了。孤單地杵在月台上,竟感覺到秋風掃落葉的淒涼感。
我緊緊抓著媽媽的衣角,想從她身上取得安心感,但媽媽卻一臉迷茫地望著前方。我跟姊姊對視了一會兒,兩個人突然都有點想放聲大哭。
「啊!你們怎麼沒上車?!」
忽然間,月台另一頭傳來大嗓門。循著聲音望去,是一身筆挺制服、戴著硬殼帽子的站務員,他嘴裡的哨子都還沒放下,驚訝地望著我們。
媽媽捏著車票,向走過來的站務員問,原本要去屏東潮州,但剛剛的火車是往臺東,想說以前這班車都是往枋寮,怕搭錯車,就不敢上去了,現在應該去哪個月台重新搭車啊?
站務員解釋,南迴線今年剛剛通車了,那輛車最遠開到臺東,所以上面才會寫臺東,但其實跟以前的枋寮路線是一樣的啦,放心放心。
他接過媽媽的車票仔細察看,再抬頭瞧了瞧月台時鐘,建議我們直接改搭等一下進站的火車,因為那輛也有到潮州,不必換月台,也不必換車票。站務員一邊解釋時,一邊隨口問:「初二回娘家嗎?哪裡來的?」
「對啊,回娘家。我們從澎湖來的。」雖然還沒搭到車,但媽媽的聲音聽起來鬆了一大口氣,我原本想哭的情緒也被安撫了下來。
站務員先是面露驚訝,接著熱情地直說自己老家也在澎湖,長大後才到高雄工作。然後,他的視線從個頭最高的哥哥,掃到居次的姊姊、矮小的我、抱在媽媽懷中的嬰兒弟弟,以及媽媽腳邊的三層大行李袋,用敬佩的語氣說:「啊~你不就一個人帶四個小孩,從澎湖搭飛機來?伍告敖!」
媽媽的嘴角咧出招牌羞赧笑容,露出一顆顆排列得整齊又大顆白淨的牙齒。當年她在美髮店當學徒時,客人總是連連稱讚她那排美齒,說一看就是好命相。
站在旁邊的我,努力地跟姊姊一起用力抬著行李袋,想讓站務員看到這畫面,讓他知道:我們都幫媽媽提行李,我們也很敖。
此時,月台逐漸聚集了新一批候車旅客。轟隆轟隆轟隆,新列車又進站了,外頭一樣寫著「往臺東」。站務員再度走回月台另一頭,嘴裡咬著哨子,對我們揮手示意搭車,也是道別。
終於可以搭火車了!
可是車廂裡人擠人,我們擠得上去嗎?媽媽一手抱著弟弟,一手提著行李袋擠上車子,哥哥和姊姊則緊跟在她身後,也順利擠上去了。而我,因為太害怕列車與月台間的那個大間隙,就這樣呆站在月台邊,不敢把腳跨出去,怕會一腳踩空,摔進黑黑的鐵道裡。
忽然間,我的腋下被一雙大手穩穩地托著,對方把我抱起來越過那個間隙,再把我安全地放在車廂裡。害羞地緩緩抬頭,想看看究竟是誰出手相助,但對方已經不見了,是男是女都不曉得。
沉浸在害羞的情緒不到十秒鐘,一抬頭才發現,前面、後面、左邊、右邊,通通都被高大的人牆團團圍住。當時個頭剛好位在成年人腰間位置,只要一轉頭,鼻子就會不小心掃到對方的肚子或屁股,只好全程維持同一個姿勢,不敢輕舉妄動。
但擠在人群裡的我,看不到媽媽她們,該不會走散了吧?新年才過沒幾天,就要跟家人失散了嗎?
正在努力透過人群縫隙,拚命尋找其他家人的蹤跡時,忽然聞到一股濃厚的氣味飄散而來,還混雜著車廂內已然高濃度的汗水味與二氧化碳。臉的位置剛好處在搖滾區第一排——正對著許多大人的屁股——的我,立即明白那是什麼。
「有人放屁,好臭哦!」捏著鼻子,忍不住脫口而出。
或許是聽到我的聲音,前方隔著約兩、三個人頭的距離,一隻小小的手掌,從人群裡探出來,一邊對著後方的我不斷揮手,一邊用氣音說:
「妹呀,是你嗎?我在這裡。」
是姊姊的聲音!雖然看不到她的臉,但媽媽她們應該都擠在前面不遠處,只是被人群擋住了。原本有點慌張的心情,瞬間緩和不少。
◇◇◇
在充滿汗味、二氧化碳以及人體新陳代謝味的車廂裡,與其他人一起搖搖晃晃約半個鐘頭後,抵達了潮州火車站。跟著下車人群走到車廂門口,看到姊姊她們已經下車,站在月台上等我,而媽媽懷裡的弟弟正睡得香甜。能在這麼擠又這麼臭的車廂裡睡得這麼安穩,弟弟也真是不簡單。
跨出車廂前,我刻意抬高下巴,讓視線盯著前方月台的灰色水泥地,不斷告訴自己:「沒事的、沒事的,別管那個黑黑的洞。」然後深吸一口氣,努力把小短腿邁開最大步——終於跨越間隙,站上月台!
呼,外頭的空氣真的好新鮮,外頭的世界真的好空曠啊。
我們跟在媽媽的後頭,三個人幫忙提著大行李箱,箱子底部不斷與地板摩擦,發出唰唰聲,就這樣一路唰到附近的公車轉運站。那裡同樣擠滿了人。有些旅客不想等公車了,乾脆招來計程車,把大包小包丟進後車廂,兩手輕便又優雅地跳上計程車。
看著一輛又一輛的小黃駛過眼前,我轉頭跟姊姊說:「我只坐過一次計程車耶,好想再坐看看喔!」姊姊得意地掰著手指說,她坐過兩次計程車喔。
此時,媽媽突然「啊」了一聲,慌忙地在小錢包裡翻找錢幣。
怎麼了嗎?媽媽為什麼又變得這麼慌張?我們走錯站牌了嗎?還是公車今天不來了呢?那……可以搭計程車嗎?
翻找錢包一陣子後,她忽然想到什麼,神色鎮定下來,走到我跟姊姊身旁,用刻意壓低的聲音解釋,弟弟是小嬰兒不用買票,哥哥有身障手冊可以免費搭車,我和姊姊要買兒童半票;但媽媽帶的錢不夠,只夠買一張全票。
所以……我跟姊姊要怎麼辦?我們要被丟在公車站嗎?還是我們兩個得自己走路到阿嬤家?
我倆的表情愈來愈不安,這次真的快要哭出來了,媽媽卻老神在在:
「無要緊啦。媽媽教你們,旦幾壘排隊時,你們排在別的大人後面,阿捏他們上車投錢時,司機就會以為你是他們的囝仔,阿捏就不用付錢啦!」
媽媽悄聲叮嚀一番後,公車正好來了,候車人潮排成一條長長的人龍。我跟姊姊分別排在兩位不認識的大人後面,姊姊排在隊伍的前段,我在中段。儘管彼此隔著一段距離,但還是能清楚看見,姊姊的兩撇眉毛緊張地向內縮,像兩條委屈的蟲。
而我的眉毛也像兩條委屈的蟲。
很少流手汗的我,雙手掌心濕漉漉一片,不斷地往褲子兩側抹。如果,我是說如果,如果我們被抓到了,我跟姊姊會怎麼樣?會被送去警察局嗎?如果警察生氣地問我,我該說是媽媽教我們這麼做的嗎?
姊姊時不時回頭,眼巴巴地望向排在隊伍後段的媽媽;但媽媽手中握著零錢,一直看向遠方,不知道是在欣賞天邊雲朵,還是在逃避我倆的求救目光。
輪到姊姊要上車了。
她轉頭與我對視了一眼,彼此交換心中的不安;接下來的畫面,在我眼中彷彿以 0.25 倍速慢動作播放——
姊姊頭低低地,爬上公車的階梯;先踏上第一階,再踏上第二階;然後,安靜地等待排在前方的大人,等對方將手中零錢「鏘——鏘鏘」地投入司機右手邊的投幣機後,姊姊再頭低低地,不敢看司機的眼睛,將身子轉往左側,越過司機,走進公車內。
萬歲!!姊姊成功搭上公車了!!
姊姊站在公車裡,透過車窗向我投來鬆一口氣的眼神。她的西瓜皮瀏海被緊張的汗水浸溼了,變成一撮撮的分岔瀏海。
幾分鐘後,我仿效姊姊的模式,頭低低地爬上公車階梯,頭低低地等待前方大人投零錢,頭低低地將身子轉往左側,頭低低地走進車廂裡。
我的瀏海雖然比姊姊還短,但順利坐上公車後,才發現瀏海同樣變得濕漉漉,牢牢地貼著額頭上緣。害怕歸害怕,不曉得為什麼,也有一絲絲闖關成功的興奮感。
車門關上,公車啟動,緩緩駛出客運站。
太好了,確定司機不會來查票了。車窗外的景象,逐漸從鬧區大馬路,轉為一塊又一塊的鳳梨田。只要再搭一段路,就會到阿嬤家了。
可能是見到我倆偷渡成功,也可能是聞到空氣中熟悉的鳳梨味,坐在公車裡時,媽媽的表情變得很舒坦。
◇◇◇
阿嬤家的站牌到了。媽媽拉下車窗上方的拉繩,拉繩發出一聲尖叫。公車停靠後,我們一個個跳下車,跟在媽媽的屁股後頭,沿著熟悉的路邊小徑,拖著行李箱唰唰唰走向阿嬤家。
「剛剛好恐怖喔,好險好險。」姊姊彷彿心有餘悸,不斷地喘著氣。
「我也是。你看,我的手都是汗。」指指自己褲子兩側口袋附近的布料,那裡明顯被水氣磨出一道深色痕跡。
走著走著,隱隱約約看到阿嬤家三合院的低矮圍牆,哥哥興奮地大吼大叫向前衝。還沒走到三合院,已經聽到前方不遠處,傳來鐵紗門被打開的「嘎——吱——」聲;再往前走幾步,看到阿嬤、阿公從廚房走了出來,笑笑地站在埕裡,迎接初二回娘家的我們。
那晚,一家五口睡在阿嬤白天擦得亮晶晶的大通舖上。自從弟弟出生後,很少有機會睡在媽媽身邊,所以那天一洗完澡,我立刻提早卡位,搶佔媽媽旁邊的位置。
身體很疲累,但大腦仍不斷轉著白天一路搭飛機、搭火車、搭公車的種種景象;翻了個身,聽著哥哥和姊姊的打呼聲,聞著阿嬤家房間的淡淡木頭香味,聞著媽媽身上的氣味,我漸漸地沉入半夢半醒,但仍惦記著明天一早起床後,要跟媽媽說:
媽媽,下次買會「叩叩叩」的行李箱,好嗎?
還有,以後不要再叫我跟姊姊搭霸王車了,好嗎?